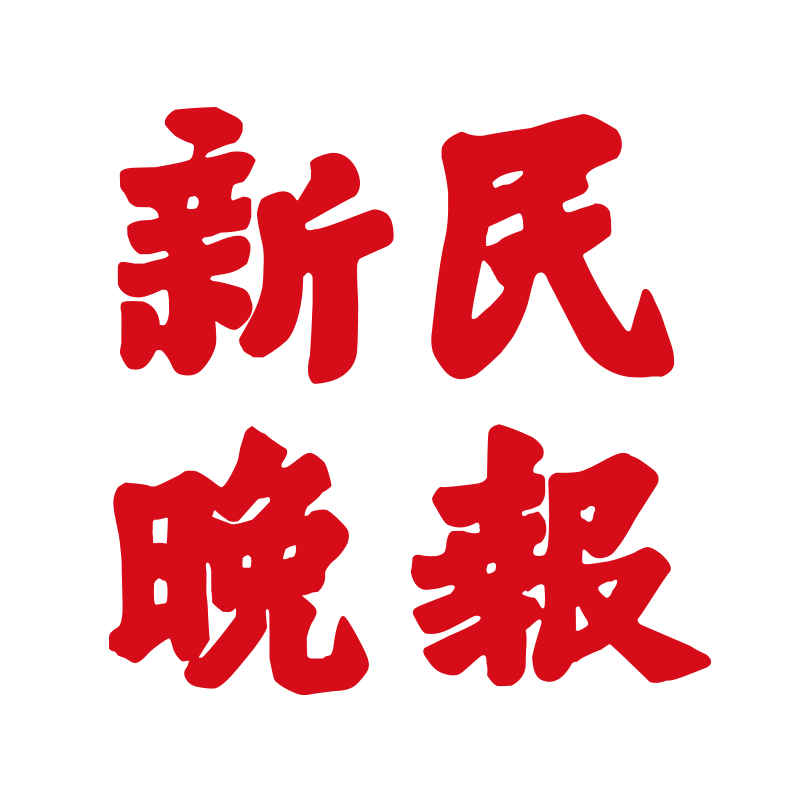假期在家时,母亲常常会做一道匪夷所思的料理。将新鲜的猪后腿精肉切成细条,撒酵母粉、白糖、山粉拌匀后,用晒干的箬叶将它们包成粽子,细瘦的长条形。只不过,这粽子里没有一粒米,我只好将其称为“全肉粽”。“全肉粽”并不用来蒸煮,而是埋进南方土灶下的草木灰,盖上柴火燃尽后的火红炭火,慢慢煨熟。除了用精肉作料,也有用腰花的,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将白糖换成盐。腰花粽倒有个新奇古意的名字,唤作“盐帖”。令人想起《韭花帖》。
母亲说,“全肉粽”和“盐帖”开胃。这好像是山中方圆几十公里的母亲们都掌握的养育健康孩子的秘辛之一,虽然她们也说不出具体原理是什么。出了这几十公里的天地,这秘辛便完全不为人知了。
火红的炭火把热度传导进草木灰、箬叶,箬叶中的精肉与酵母粉、白糖、山粉慢慢融合在一起。这个过程十分漫长,通常要一两个小时。母亲牢牢掌握火候,到一半时间时,便拿着火钳子拨开炭火和草木灰,将粽子翻个面儿,又重新盖上草木灰和炭火,再烤一半时间。这样的时刻,烤熟的那一半,香味已若有似无地蹿出来。这是一种什么味道呢?箬叶的香,混合着酵母白糖精肉的香,是一种馥郁的火的味道。它从灰不溜秋的灶台后一直飘出厨房,来到客厅,最后来到院子里。我说,这香味会打转。母亲笑,那是你长了狗鼻子。太灵。
待到整个粽子烤熟,打开已松松脆脆的箬叶,那可真是一枚香气的炸弹了。
母亲说,是火的香味。
很多年后,我长居城市,经久不见明火,不知是谁问我,火是什么味道?我脱口而出,火是香的。那几年,尤其爱喝岩茶,只因岩茶有熟悉的焙火香。
遥远如梦境的黄昏里,精瘦的父亲在院中用斧头劈开松树圆段,手指大小的白色松蛹跌落在地。大约是不习惯这突如其来的天光大亮,它们胖嘟嘟的身体只好扭来扭去。母亲迅速将它们搁在火铲上,伸进火势猛然的灶膛。松蛹一下子被烤得焦黄松脆,香气四溢,是山中上好的零嘴。
还有在炭火上烤玉米饼。圆形的金黄色玉米饼,里头塞进油黑梅干菜,被二伯和凤凤伯母带进高山的油茶林,作为干粮。天不亮时,他们便合上家门,在晨光熹微里裹着露水来到自家的油茶林。深秋时,油茶果缀在枝头,沉甸甸的。我们如猿猴在枝丫间攀缘、摘取。而幼小的我,会一遍又一遍地表达自己的馋意:你们饿了吗?我们吃午饭了吗?二伯明了我是冲着玉米饼早起上山,只是从不点破,早早在林间空地生起篝火,等火势渐熄,他便拿出准备好的玉米饼,放在炭火边的石头上炙烤。不一样的火的香味。玉米粉的香、梅干菜的香、石头的香,甚至密林中阳光的香,烫嘴的香。
年迈的祖母则热爱烤一切。烤栗子、烤土豆、烤蒜,她甚至烤鸡蛋。冬日时,她和祖父坐在祖屋厅堂的躺椅上,一人一边。她将一双手拢进双腿间,底下一只竹篾编织的火熥。我们永远猜不到金属盖子上搁着什么小玩意儿,只偶尔听见“bang”的声响,有什么香气炸开来。
火的味道。父亲大约最熟悉了。
年轻时,他不知从哪里知道,一种土称乌木烧制出的炭火,可高价出口到日本。那些年,他便垒窑与炭火为伍。形态古老的窑,顶部隆起,门小小的,是一种年轻的遗址。从装进乌木到炭火裁切完运送出山,一窑炭火要花上半个月。
窑总是火热的。窑温未褪尽时,父亲便要把柴火竖着叠放,填满整个窑洞。那种余温,把父亲变成水,不停流的水,绞干他身上原本的年轻丰腴。窑口是封闭的,父亲好像通过闻去确定火候。他说,乌木在成为炭火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味道。火候成熟才准备出窑,慢慢打开封闭的窑口通入空气,乌木逐渐燃烧,窑膛内渐渐明亮,黑暗被全然驱逐,只剩晃动的火红。排列的乌木褪尽木的厚实,炼成金属一般精瘦的身躯。一如我的父亲。
在这熊熊炭火中,我们一如既往,把地瓜、土豆埋进草木灰。(松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